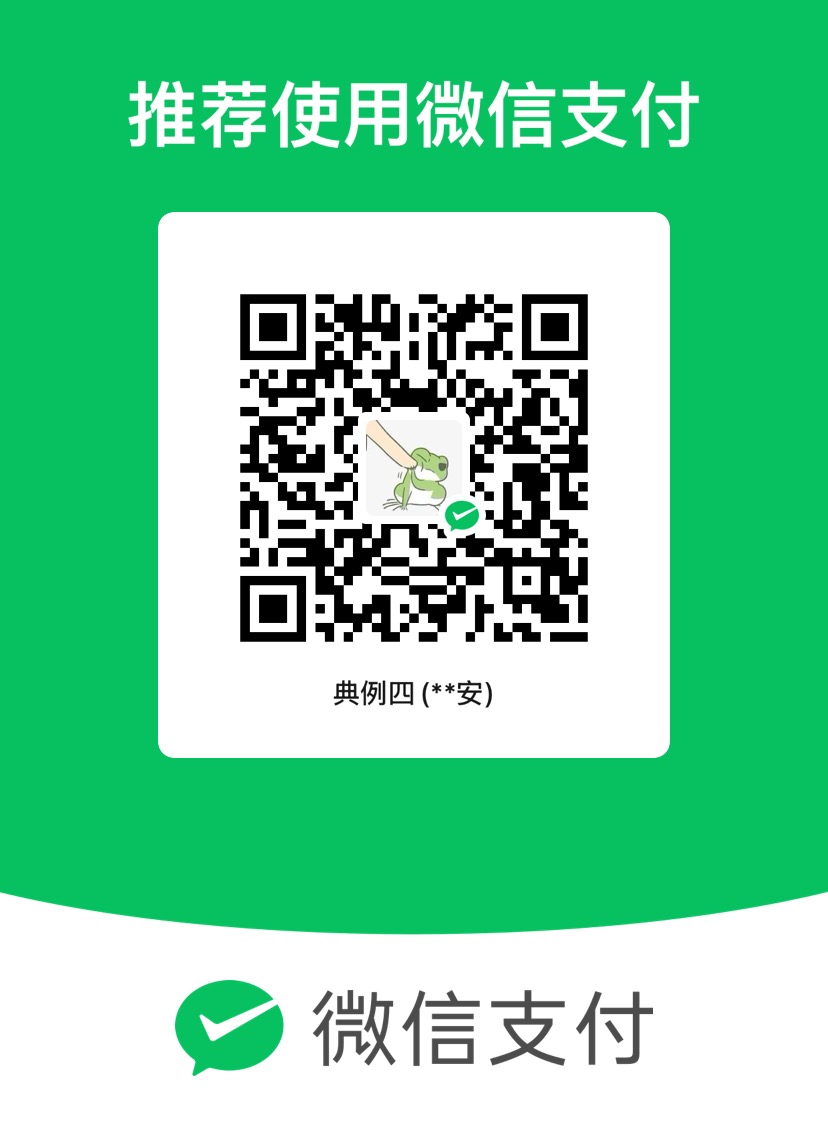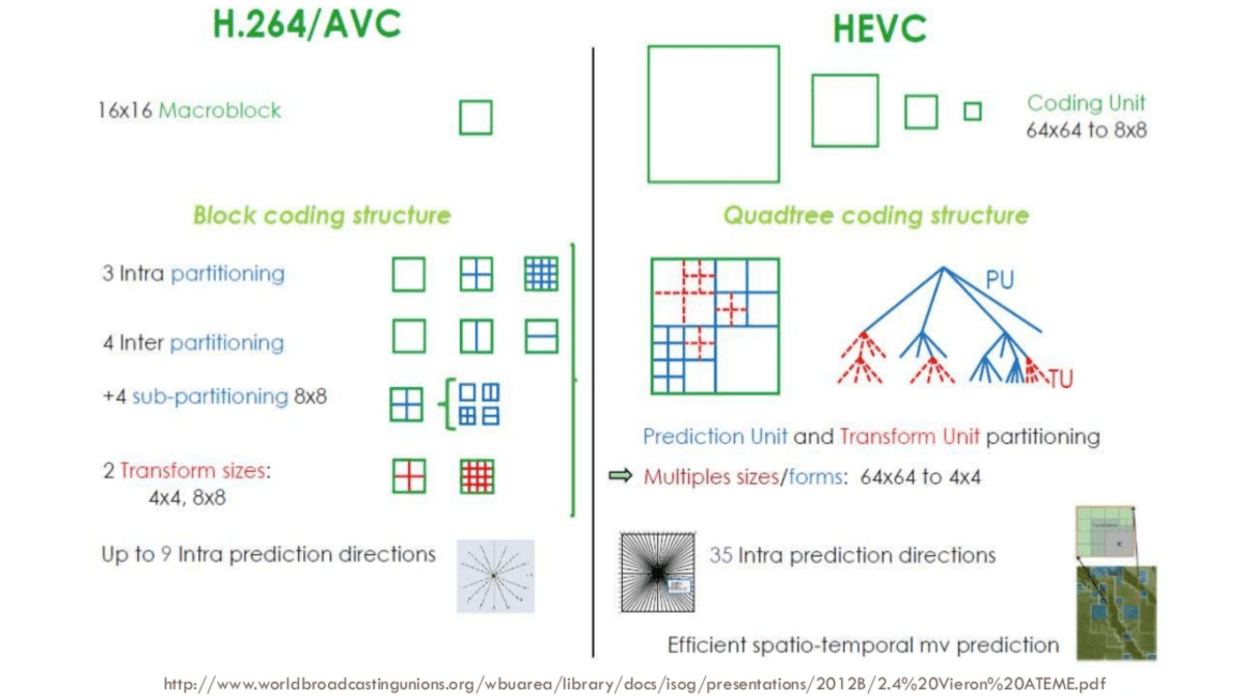加入实验室
第一学期初我申请了导师实验室的入门许可,一直拖拖拉拉没有正式收拾出一个工位。觉得自己并没有正式的国大学生身份,行动上也并不积极。
组里有国内交换过来的博士生,我们很快建立了联系。因为入门许可批准需要一段时间,最初由我来协助他实验室进出,顺势我便正式布置了工位。自此,久留的地方从utown转移到了工位。我在尝试融入。
组内有两间实验室,其中一间紧挨导师办公室。开完组会,透过门缝,室内熙熙攘攘交谈声不断。而我所在的实验室修在另一栋沿山而建的教学楼中。光线相对较暗,显得冷清。第一学期实验室里人很少,几乎只有我和学长长时间在工位,偶尔有其他博士生和研究助理工作;杂物很多,还有一台和我年龄相仿的惠普打印机,和上届博士生传下来的床垫,一来形成鲜明对比。难免失落。但也得益于此,实验室并没有例行的检查,形式也相对自由,非实验室人员来往密切,我借机也认识了许多人,对我博士的申请有很大的帮助。
寒假期间,我回国休整,收到了实验室群发邮件,要求成员及时认领个人杂物。庆幸自己没有将同学因腾空宿舍而无处安置的日用品放在实验室里。
来年返校,实验室整洁了许多,换了新的日光灯,每周还会有专门的保洁来打扫。不到两周,实验室里的人就多了起来,常驻的不再是我和学长。导师联合指导的实验室变得热闹,不断的有新的交换生和博士生入驻。那台打印机不知去向,但先前空荡荡的白板每天总是填满了不一样的公式和草图。我的旁边也多了一位来实习的本科生和一位是国大的博士生。屋内有三排桌子:我在中间一排;靠门一排除了学长,还新来了三位来法国的博士生;靠窗一侧的床垫蜷缩在讨论桌下。室内开始有了装饰,贴上了带着专属logo的海报。与中国的学生不同,新来的他们显得更松弛,氛围变得轻松许多,像从北地的晨晖切换到了南欧的阳光。
第二学期我完全处在了外语环境中。导师鼓励我多与他们交谈,跳出舒适区。法国来的他们与我并不是一个项目组,但也时常邀请我加入到他们的讨论会,会后一起用餐。得益于我“模糊”的学生身份,我有充足的理由解释自己英文不好,这为我带来了能让他人耐心听完我讲话的“特权”。此刻,语言已更本质的形式被领悟,回归到交流本身。虽然我敢肯定经过长时间的相处,我的词汇量下降明显,但是表意能力比半年前好了很多。我在适应不同交流模式的切换。
似乎不再羡慕另一间实验室。或许八月份再次入学后的我还会选择这个半年前刚刚整理好的工位。